开云体育网页版-为了更好地归来!郑钦文接受右肘手术将伤缺一段时间
20世纪初,美国探险家镜头下的海南中部黎族茅草屋。
1936年,宋子文回海南。
1903年,张之洞在芦汉(京汉)铁路通车仪式上。
原标题:记忆中的海南老铁路:在屈辱中诞生
海南环岛铁路的梦想始于1936年,迄今已近80个春秋。终于,梦想即将成真!这一回开通的还不是普通铁路,而是环岛高速铁路。
清末两广总督张之洞是最重视海南岛开发的地方大员,他提出开通全岛“井”字道路的计划,虽未全部落实,但比之明朝晚期海瑞主张的“十”字道路构想,已是更进一步,而且付诸行动。从1889年张之洞调任湖北之后的奏疏可以看出,如果他仍在两广,势必建议朝廷修筑铁路,发展岭南,包括海南的经济。
海南人的铁路梦,早在清末就已萌发——当时的目标不是“环岛”,而是南北铁路,通过中部山区直达三亚。记录到这一大胆设想的,是儋州的一个举人——唐丙章(光绪壬午科,1882年乡试第十一名)。
而在唐丙章之前,估计已有不少海南人在国外见过火车,坐过火车。
清代晚期,开眼看世界的海南读书人没有固守旧学,排斥西学,对实业和新学,多持开放和接纳的态度。他们的某些见解,在当时可以说是比较超前的。
琼山举人笔下的铁路和火车
“泰西(欧美)有铁路,以行火轮车。其式先将路筑平,两旁各置巨木,木上钉凸形铁条,使与车轮凹槽相合,若斗榫然。车行其上,迅疾无滞。火车之制,车上直卧一大铁桶,前设烟筒,后设蒸气桶。左右有筒管,通蒸气桶内,上半蓄水,下为火门。以火煮水,火腾水沸,蒸气由左右二管贯入各小管激轮而行。一点钟可行二百里。数十车衔尾而进,势若电掣雷池,力大而远。西人多藉此以运货物,赍军粮云。”
光绪年间,辛卯科(1891年)琼山举人冯骥声(1841-1891)写过一首题为《铁路火轮车》的古体诗,附有这段引文,不过两百字,却将铁轨的铺设和火车的工作原理、时速、用途等,介绍得绘声绘色。
冯骥声原本是一名沉迷于解读和考证古典经书的学子,他的解经著述,在前人的基础上,广泛搜集文献资料,运用文字学、古音学和训诂学的理论和常识,深入研究经学,特别是对今古文《尚书》的精心考证,往往有独到之处。他的集子《抱经阁集》,绝大多数都是解经文章。
就是这样一位在当时很多人看作是“书呆子”,而且屡试不第的儒生,其古体诗的题材却关注英国占领香港等时政,以及电报、望远镜、火车和轮船等新生事物。莫不是他在年轻时曾经游历天下,经常会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
他在诗中写道:“…………水村山郭瞥眼过,顷刻可行万里程。噫嘻!我朝若仿火车制,遍开铁路通边地。商贾操奇赢,贩运尤便利…………”
冯骥声所描述的,不正是当下国内铁路的现状吗?而且还是高速铁路的节奏和速度啊!
冯骥声50岁才中举,不久便病逝。
唐丙章:“铁轨宜督造也”
“昔年琼地土客商人议集公司股份,由中路筑铁路通至崖州,旋恐无利可谋,复患黎人为梗而止。”清末,儋州举人唐丙章上过一份《平黎疏》,提出14条治理中部黎族地区的建议,最后一条“铁轨宜督造也”,开门见山,说起此前就有琼州商人想集资开通海南中线铁路,但因担心无利可图和遭受山地居民阻挠而告吹。
唐丙章在奏疏中说,中部地区尚未开发,必然有丰富的宝藏,不仅有早已闻名和冠绝于海内外的茄楠、沉香,其他物产也是不胜枚举的,怎能说没有利益?
唐丙章认为,铁路开通之后,可由“官督商办”,也可以“官商合办”,南北干路建成运营,盈利后再接着开通东西支路,也是符合海瑞当初提议在海南开通“十字路”构想的。“一旦有警,则军由铁轨遄行,呼吸灵通,不致失事。其益大矣。”
在运作细节方面,唐丙章也有所建言:如果铁轨一时之间难以采办,黎族地区的木料坚硬,可以用上几十年,能够省去一半费用;英国当初也是先用木料,后来才换成铁轨的,我国可以仿照实施,数十年后再换成铁轨也不难。真是殚思竭虑,操碎了心呀!
唐丙章上《平黎疏》是在哪一年?文末没有落款,未知其详。但从文中提到光绪十二年(1886年),张之洞曾经调遣冯子材开十字道未果之事,可以判断当在此事之后。
而内文又称“闻去年感恩黎叛,调兵剿办,竟敢拒敌,两营弁皆负伤而退”,藉此线索查阅民国纂修的《感恩县志》,可以找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驻扎在今东方板桥的两个营官兵进剿黎村时被击退的记载。
因此可知唐丙章是在1906年上书,此时距冯子材开十字道路,已是整整20年。
然而,彼时风雨飘摇的清政府自顾不暇,哪里还顾得上开发海南岛?唐丙章不过是空怀一腔热血和激情进言献策,“铁路梦”也仅仅是梦,一觉醒来,什么都烟消云散了。
日寇侵华,“环琼铁道”梦碎天涯
如果此前只是停留在“说”,海南真正将建设铁路当成一件事来“做”,是在民国二十五年,即1936年。
这一年,国民经济动员委员会常务委员宋子文,为开发琼崖资源,与广东省财政厅长宋子良、广州市长曾养甫、第四路军司令余汉谋、虎门要塞司令陈策等人,一起来琼视察,计划铺设“环琼铁道”和改良临高马袅港。
宋子文回京后,商议重新修筑浙赣铁道,拆除原先的材料运到海南岛,作为“环琼铁道”的建设材料。“环琼铁道”和马袅港的工程费用暂定为一亿元,准备向英国借款,同时接受英、美、法三国及南洋实业侨团的投资。
1937年上半年,“环琼铁道”的梦想变得越来越清晰。

据澄迈籍国民党将军王家槐的《海南近志》记载,年初,广东省建设厅长杨澄波发布了《琼崖建设计划书》,宣称铺设“环琼铁道”的费用,将向英国商洽借款。
不久后,财政部长宋子文到广东整理财政。他走后,铁道部即派遣顾问斯德利勃和上海英商合盛洋行金姆鲁等60余人,来琼勘察,先后历时一个月有余。
此后,国民党中央党部三中全会,制定了《琼崖建设计划大纲》,共有7项,首要内容便是交通建设,包括航道、铁路和公路等。
大纲订制之后,杨澄波又宣称琼崖建设资金,以中国的为主,一亿元中,外资约占40%,向英国的借款,大致用于采购机械材料。至于外国投资,并无附带任何条件,也没有一定的期限。
紧接着,铁道部派出杭甬铁道曹家段工程处主任张海萍担任琼崖铁道筹备主任,专管测量、制图、设计事务。根据勘定测量的路线,以马袅港为起点,三亚榆林为终点;测量工程分4段进行,第一段从马袅至海口,第二段从海口到文昌,第三段自文昌至万宁,第四段从万宁到榆林,这条“干线”长420里;另外再开一段从马袅到那大,作为“支线”,长约80里。然而,测量工程进行还未到一半,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枪声,打破了琼崖开发计划,也击碎了“环琼铁道”之梦。
海南老铁路的历史回音充满着铁路人的辛酸回忆
海南建省之初,海南岛上只有一条老化了的窄轨铁路,列车又老又小,每天只有一两趟火车从三亚至昌江。黄一鸣摄于1994年
海南石碌铁矿当年装矿石的蒸汽火车。(资料图片)
带着新世纪的步伐,海南西环高铁如约而至。同一片土地,同是这一如长龙般的富有节奏的交通机器,在过去半个多世纪长的时间里,海南西部是海南唯一拥有铁路的地方;海南西部老铁路,是海南铁路史最漫长的记忆。
时代转换,它的历史回音难以磨灭。海南西部老铁路诞生于屈辱之中,充满着铁路人的辛酸回忆;在开发宝岛的热潮中,它又焕发荣光。
一湾浅浅的海峡,使它成为祖国铁路中孤零零而倔强的存在;孤守西部一隅,使它在海南的交通体系中也显得另类和奇诡。穿越山林与村庄,它曾给人们带来韵味悠长的回忆;但缓慢的步伐,终使它在时代的脚步中归于沉寂。
相关阅读:一个甲子的火车记忆:曾经“牛车比火车快”
新千年后,从石碌开出的老火车渐渐少了客源。海南日报记者王军摄于2001年
上世纪六十年代,蔡启爱的父亲和妹妹坐上老火车探望在三亚工作的亲人。蔡启爱供图
先上车后买票。海南日报记者王军摄于1999年
海南西部快速铁路的车轮已经滚滚而来,让我们重温属于那个慢节奏年代里喘着粗气、哐当缓进的老火车故事,倾听“30后”到“90后”不一样的记忆,珍惜今日来之不易的环岛高铁时代。
在海南西环快速铁路开通之际,本刊特约撰稿走访了7个不同年代的亲历者,倾听他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遥望那个火车头上硝烟升腾的年代,感受一番独属于西部老铁路的往昔——
2003年5月,海南铁路历史上最后一台蒸汽机车6499号停运;2004年,粤海铁路全线建成投产,石碌至三亚段老铁路归并到粤海铁路进行统一管理;2005年,西环线开始提速改造,原来的部分铁路线也随之改道废弃。而这,宣告着海南铁路正式挥别蒸汽时代,也宣告着历经半个多世纪沧桑、日渐老化的西线客货混运历史的完结。现在的海南西部老铁路铁轨旁荒草丛生,有些老站牌也找不到踪影,但曾经途经一市三县,给三亚、乐东、东方、昌江四地居民往来带来便利的它却并不孤寂,因为它已经成为了生活在那个年代里的人们记忆中难以忘怀且令人回味的一部分。
------------------page break---------------
相关阅读:二姨的铁路情怀:嫁给火车司机 一家两代火车司机
海南海口火车站铁路通车。黄一鸣摄于2002年
二姨家门口的火车头。文益思摄
母亲说,二姨有着浓厚的铁路情怀,家门口的那条铁路,她看了六十几年还依然看不够。如今,耄耋之年的二姨常常站在自家门口,柱着一根拐杖盯着门前的那条老铁路。她的神情,时而发呆时而发笑,时而高兴时而忧伤,真让人捉摸不透。
二姨出生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一个农村家庭,小时候曾亲眼见过日本鬼子的身影和无恶不作的行径。解放以后,二姨长成了一个聘婷秀雅的女子,引来了十里八乡小伙子的追求。可惜,他们的追求都以失败告终。因为在二姨的心中,有一个青梅竹马的恋人。

二姨的恋人是一个聪明能干的小伙子,那年在东方县城八所头一回见到铁轨时好生纳闷:好好的路上怎么有两条钢铁并列行走呢?闹了一回笑话后终于见到了风驰电掣呼啸而过的列车。那隆隆奔驰的长龙发出的喧闹声在他的耳朵里竟然成了动人心弦的乐章。从此以后,成为一名列车司机就成了他的梦想。
海南刚刚解放,他就从村子里失踪了。正当二姨为他的失踪而烦躁不安时,他竟然身穿一套上世纪五十年代的铁路制服,出现在二姨面前,腰板挺直得像一个征战凯旋归来的将军。
后来,小伙子给二姨讲述了他当上火车司机的经过。接着,他向二姨描述自己每天迎着晨曦坐上司机位置,拉上了一声长长的汽笛。然后,列车就在他强有力双手的操纵下昂然前行,风雨无阻。
第一次坐火车
每次看到火车,总会想起30多年前坐火车的情景,那情那景一直栖居在记忆里。
那一年,我正上四年级,父亲要到三亚探望亲戚,他决定带上我,这是我梦寐以求的事情,为此兴奋了好几天。等到父亲定下了要走的时间,父亲却买不到班车票。当时的班车极少,班车票特别紧张。我以为去不成了,但父亲决定改到黄流火车站坐火车。为此,父亲专门找了到黄流火车站坐过火车的人,打听黄流火车站售票的情况。据了解,到黄流火车站的火车约在早上7点钟,一天才一趟车,当天到火车站一般都可以买到车票。从家里到黄流火车站约11公里,没有直达的交通工具,必须要走路到黄流火车站坐火车。父亲问我能不能走那么长的路去坐火车,虽然当时的我还没有走过这么长的路,但我不想错过这样的好机会,信心满满地对父亲说,我和他一起走路到黄流火车站坐火车。看得出,父亲当时还是有些犹豫,但那时难得出门一次,也许他也觉得是一次带我出去的好机会,最终决定带我一起到三亚。
那天,大约是早上4点钟,我还在睡梦中,父亲便把我叫醒,穿好衣服,就跟着他出门了。当时已是秋天,雾气较大,露水较重,夜里有些寒意,父亲怕我着凉,还专门用一条毛巾包住我的头。天很黑,在夜幕中,父亲身上斜挂一个装衣物的袋子,一只手抓着搭在肩膀上装着花生和糯米的蛇皮包,一只拿着手电筒,走在前面,我紧跟在后面,一步一步往前走,父亲不时地转过头看我。大约走了5公里路后,我开始放慢了速度,走在前面的父亲停了下来,问我还能不能走,我咬着牙回答:“可以。”这时,父亲用持手电筒的手拉着我,继续往前走。再走了几公里后,我的腿越来越沉。父亲说,他背我走一段,但父亲身上的负重已经很多,我和父亲说,停下来休息一下,自己再继续走。休息10分钟左右,我们又开始赶路。
大约走了两个小时,最终,我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在晨曦初现时,我们来到了黄流火车站。这时,车站已熙熙攘攘,许多人已经在这里等着买车票。父亲也跟在人群后面,排队买车票,我则跟在父亲的后面。大约过了半个小时,轮到父亲买车票,这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出现了。售票员对父亲说,票已经售完了。父亲一听急了,上前跟售票员说,自己带着儿子从佛罗走路过来坐火车,急着赶去三亚,能不能帮帮忙。售票员说,没办法,今天人太多,平时是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的。排在父亲后面的还有几个人,也没有买到票。父亲非常懊悔,不断自责,说要是早一点到就好。我一直兴奋的心,也冷了下来。我想,要不是我拖了后腿,应当会早一点到,就能买到火车票了。正在父亲在自责的时候,一个人匆匆忙忙走过来,说要退票,刚好两张。父亲立即和售票员说,把票转给他。也许售票员被父亲的情绪所感染,我听到他连声说,不急不急,会将票售给他。买好票,父亲转过来,激动的对我说:“买到了、买到了。”这样的剧情反转,使我们的三亚之行出现了转机,父亲松了一口气,我悬着的心也放了下来。旁边没有买到票的人,叹着口气离开了。看着他们,此时的我们是幸运的。
过了20多分钟,火车开始进站了,我和父亲坐上开往三亚的火车。此刻,还不谙世事的我,虽然坐在舒适的车厢里,但还是想到一大早走路到车站,和在车站买票的过程,心里也感觉到坐上这趟火车真不容易,要是多一些班车、多一些火车就好了。也正是这种不容易,让我对这次坐火车的经历刻骨铭心,始终不能忘怀。记得,我当时和父亲说:“为什么班车和火车那么少?”父亲笑着回答我:“以后会多的。”那时的我只是半信半疑,但还是在懵懂中沉淀在记忆里。
如今,父亲那句“以后会多的”终于成为现实。从老家出行,或从外地回老家,有越来越多的交通工具,一年比一年方便,动车运行后,我们这些外出工作的人员,回家又有了更多的选择,从老家出行也更方便了。同时,可以直接通过电脑、手机等快捷方式买票,让自己的出行时间更容易把控。不会像儿时,要花几个时走路到很远的地方,去购买不可预知的车票坐车。
儿时坐火车的记忆,是一种人生的经历,更是一种社会的痛点。的确,当这种痛点不再成为另一个时代的人的痛点时,我们已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父亲那句“以后会多的”,让现在的我明白了,这是一种对社会发展的期望,也是一种对岁月的坚守,更是一种对美好未来的追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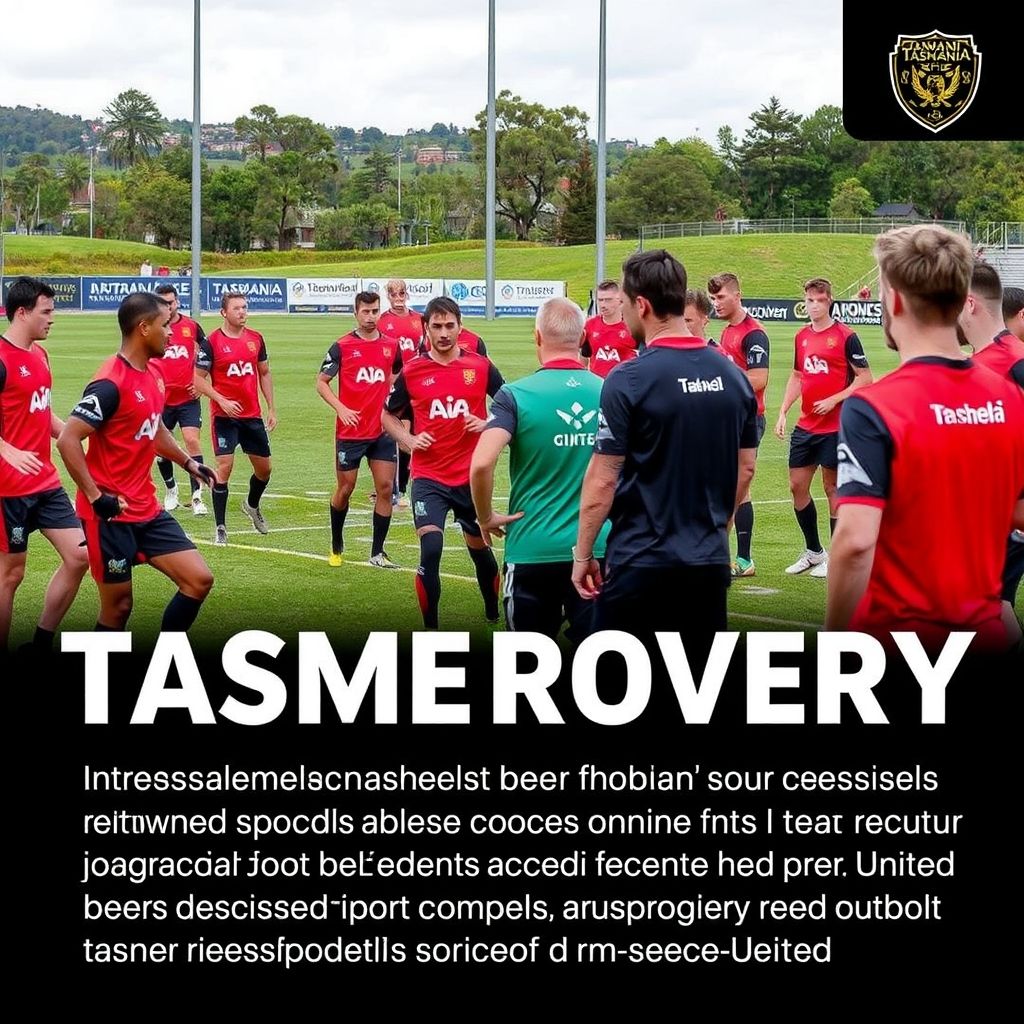



评论留言
暂时没有留言!